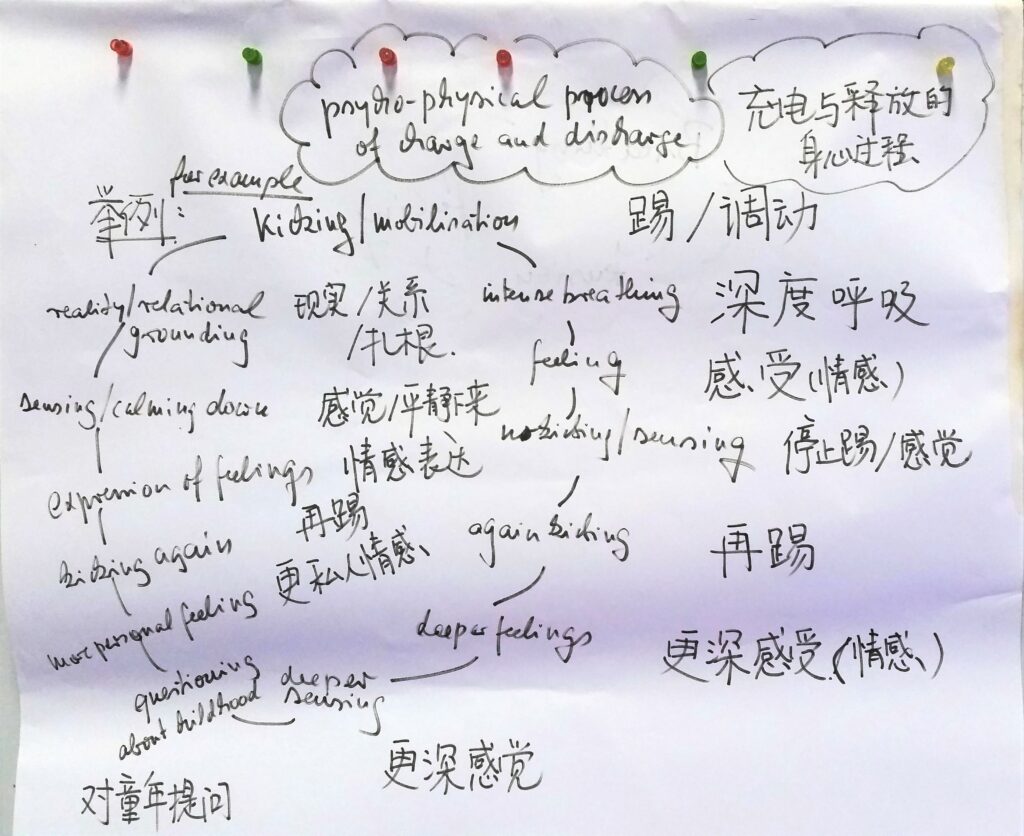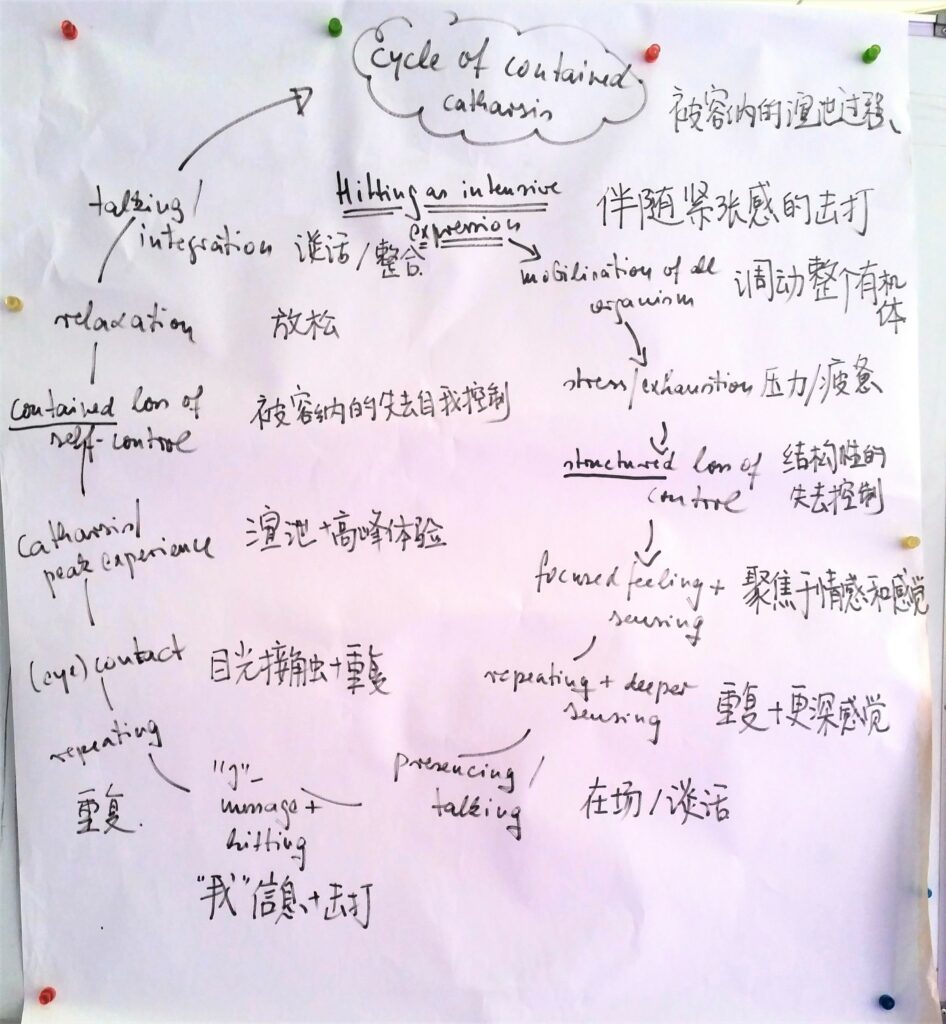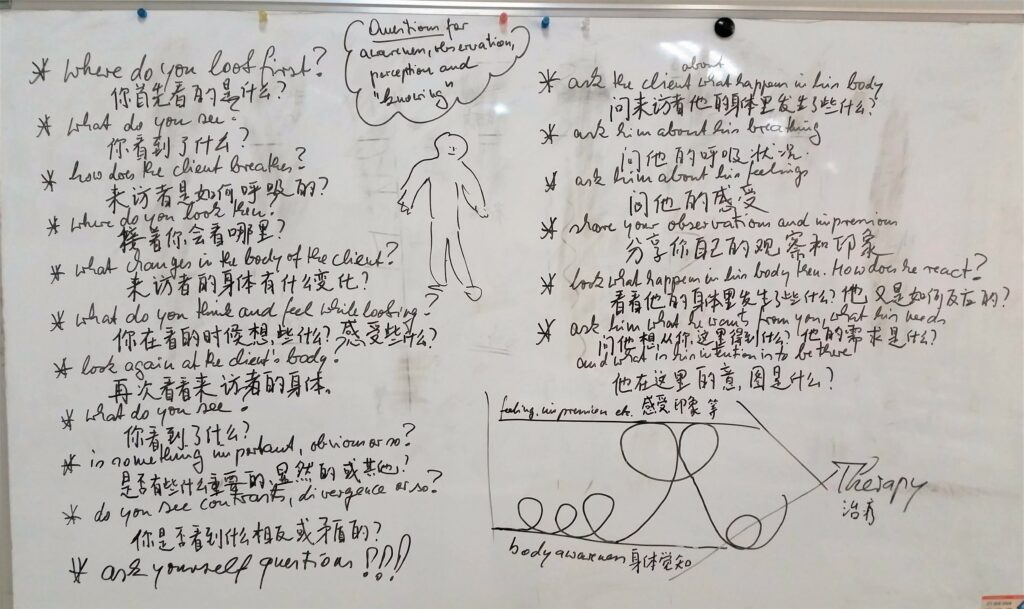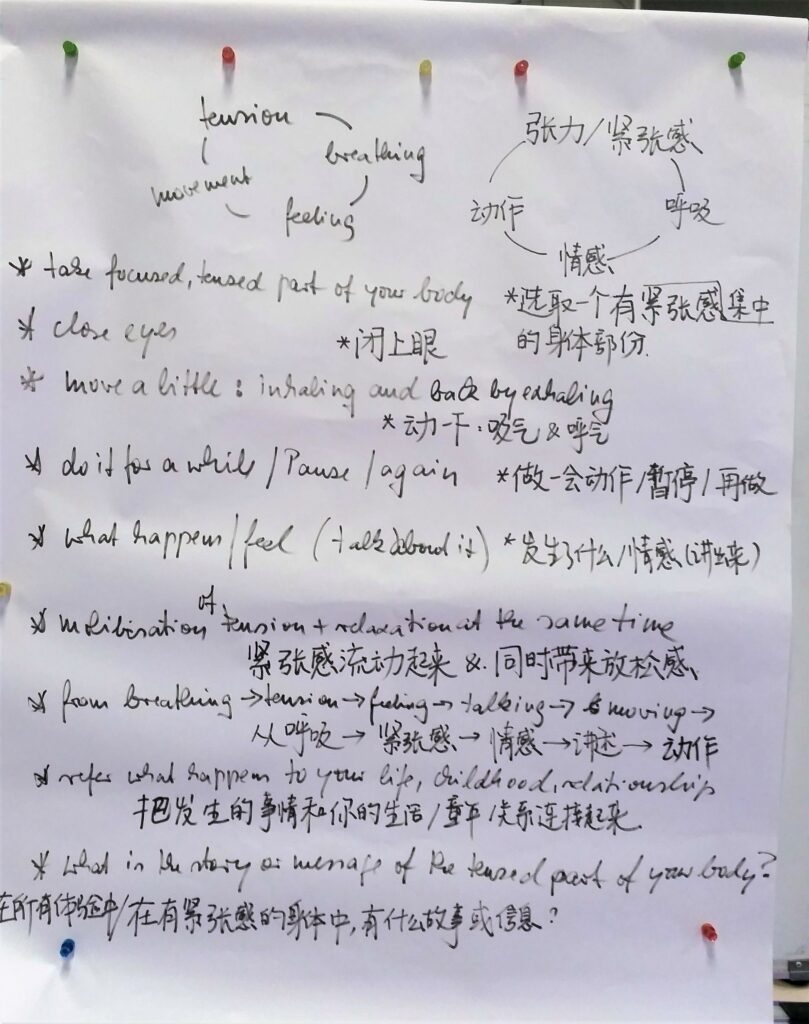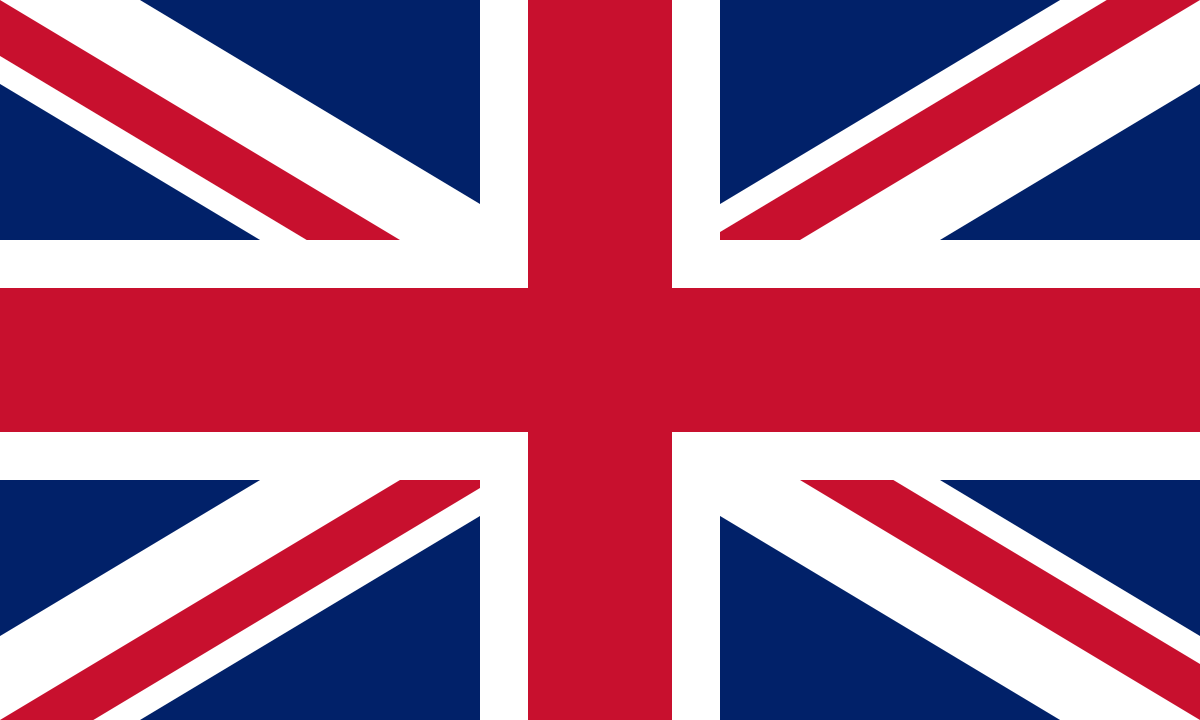Ulrich Sollmann
乌尔里希.索尔曼,躯体心理治疗师, 心理执行教练与公关人员, 上海政法大学客座教授,维滕大学高级研究员,伊斯坦布尔马耳特佩大学高级讲师
• 1947年出生,已婚,育有两子女
l 大学主修法学和社会科学,研究领域主要为社会学、经济学、社会心理学及心理学
l 社会科学和政治学硕士学位
l 国家认证心理咨询师
1 进修
l 肢体语言/心理康复疗法,完形心理治疗课程
l 培训师,监督师及咨询师培训课程
1 工作经验
l
• 1978年起从事健康管理,心理康复及心身医学领域的工作
l
• 1978年起在德国明斯特大学任教,并在各种国际会议发表演讲
l
• 1980年起为经济、工业及政治领域人士提供培训及咨询服务
l
• 1982年起出版个人著作,参与众多媒体节目制作
l
• 1991年成为国际商业培训师联盟(TRIAS)的工作人员
l
• 2007年至
• 2012年,经营Keese & Sollmann 咨询公司
所属组织
• 1988-2011年:德国生物能分析协会(DVBA)主席
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会员(DCAP)
国际生物能分析研究所(IIBA New York)会员
德国完形心理疗法协会(DVG)会员
德国社会政治咨询协会(degepol)会员
德国新闻记者协会 (DJV) 会员
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:国际心理治疗杂志(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therapy, IJP)
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:能量与性格
从事工作
l 针对企业高层管理人员(总裁,主管等)
- 企业管理咨询
- 管理人员自我完善培训:个性培养、管理方式、组织能力
- 抗压力培训(危机管理)
l 针对家族企业的企业管理咨询
l 针对从业人员的职业前景/过渡期咨询培训
l 针对领导人员(政党/企业)进行自我表现能力培训及宣传策略制定
l 针对企业进行员工性别结构、年龄结构和性格差异的管理咨询
l 非语言信息,性格及其相对应的职业行为模式培训
发表著作
• Since 2010 I´m intensively engaged in 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Germany. Since 2013 I constantly work in China (before the pandemic) three times per year for about two weeks each time (lecturing, workshops, professional training, coaching, publishing)
• Gest-Professor a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(SHUPL)
• Research-fellow at University Witten Herdecke
• «Bioenergetik in der Praxis» (1985)
«Visionsmanagement» (1993)
«Management by body» (1996)
«Schaulauf der Mächtigen» (1999)
«Einführung in Körpersprache und nonverbale Kommunikation» (2013), «Begegnungen im Reich der Mitte- mit psychologischem Blick unterwegs in China» (2018)
• 自2010年以来,我一直致力于中国和德国之间的跨文化交流。自2013年以来,我每年在中国工作三次(在大流行之前),每次约两周(讲课、研讨会、专业培训、辅导、出版)。
– 上海政法大学客座教授
– 维滕-赫德克大学研究学者
• „实践中的生物能量学“(1985年)“视觉管理“(1993年)“躯体管理“(1996年)“论强者的展示“(1999年)“躯体语言和非语言交流导论“(2013年),“邂逅中国–以心理学的眼光看中国“(2018年)。
•
语言能力
德语,英语,荷兰语
受聘企业(部分):
德意志银行,德国商业银行,普华永道,莱茵集团,德国汉莎,
• 正念与生机:生物能量学视角下的压力管理
我在三个社会/跨文化领域从事专业工作。我的工作是综合性的,我对人们在职业环境中的行为,人与人之间的重叠交叉性活动特别感兴趣。
这三个领域是:
– 作为一名教练和顾问,我为行政人员、管理层和 „在职的 „董事会以及政治家和政党提供支持。基本上,我专注于角色、职能和责任的互动/相互作用,以及人如何胜任他们的角色。主题包括:领导力、变革、冲突解决、倦怠、性别等。
– 作为一个以躯体为导向的私人心理治疗师,我与人们一起研究他们的问题,研究他们的个人发展,以及口头和非口头的观点,即以躯体为导向的方法来处理人的问题/难题。必须始终在两个层面上看待决策和发展。
– 工作和生活现在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公共场合或与此相关的场合。这个 „公众 „可能是内部或外部。通常这也与媒体上出现的公众有关。不管是否愿意, 人们、管理者、政治家以及企业/党派总是要面对他们的公众影响力。因此,我的其他业务领域之一是帮助人们认识到这些影响效果,以及如何产生影响(具体的和/或战略的)。
基本上,我的工作涉及以下几个方面:
– 角色(个人)和他们的具体行为模式。
– 躯体语言和适当行动的重要性。
– 语言和非言语交流。
– 显性和隐性的兴趣、需求和目标。
– 在特定的(特别是跨文化的)背景/环境下。
TRIAS 国际商业培训师联盟(国际教练、组织发展和咨询培训学院)工作人员
此外,我还通过撰写我工作中的重要问题(书籍、文章、网络博客)、在国际会议上发言、在大学教学和培训咨询师以及加入特定(专业)协会来进行交流。
– 自2010年以来,我深入参与了中国和德国之间的跨文化交流。自2013年以来,我每年在中国工作三次(在大流行病之前),每次约两周(讲课、研讨会、专业培训、辅导、出版)。
-上海政法大学客座教授。
– 维滕-赫德克大学研究学者
– 自2015年起在中国出版和发表博客。
– 介绍躯体语言和非语言沟通
– 正念与活力
– 性虐待、躯体心理治疗和羞耻感
如果你对英文出版物感兴趣,请看一下,按这里